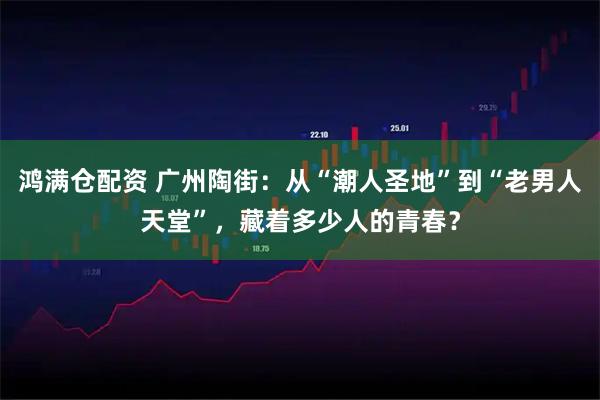
《陶街记》
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,广州城里照例是喧嚣的。新起的楼宇间,偏有几处老巷,固执地蜷缩着,像被时光遗忘的皱纹。我向来以为,要识得一座城的真面目,须得往它最旧的皱褶里钻。于是择了个阴晴不定的午后,与二三友人踱进了那唤作\"陶街\"的所在。
这街原不过二百步长短,夹在越秀老城区的腹地,恰如一枚生锈的铜钱,嵌在广州的\"城市原点\"左近。老广州人说起此地,眼睛里便会浮起一层薄雾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光景,这里是何等风光!彼时满街的音响铺子,喇叭里日夜吼着港台的靡靡之音。后生们顶着烫卷的头发,裤管大得能装下两袋米,在这方寸之地摩肩接踵。那些黑亮亮的电器匣子,在当时人眼中,简直比灶王爷的供品还要金贵三分。
展开剩余75%有趣的是,许多街坊至今仍管这叫\"淘街\"。想来也不奇怪,当年此处杂货堆积如山,从搪瓷痰盂到香港歌星海报,活脱脱一个市井版的聚宝盆。我见过有老伯在此淘得一副老花镜,戴上后竟把报纸拿倒了,却仍欢喜得如同拾了夜明珠。
而今重游,倒像掀开一本发黄的相册。那些铁皮招牌上的油漆龟裂如老人斑,玻璃柜台里陈列的录音机,活像博物馆的出土文物。偶有顾客,多是两鬓斑白的\"老男孩\",他们摩挲着蒙尘的功放机,眼神却穿过积灰的晶体管,望见了自己的青春。有个穿人字拖的阿叔对着索尼walkman发怔,忽然哼起《偏偏喜欢你》,走调得厉害,却教人鼻酸。
新城区的霓虹自然更亮些。珠江新贵们喝着英式下午茶时,怕是不会想到,三站地铁外还蜷着这么条化石般的街巷。倒是有群举着相机的年轻人近来常在此出没,他们称这作\"复古打卡\"。有个染紫发的姑娘对着破败的电器摊连拍二十张,我凑近看时,发现她手机壳上印着\"怀旧是种新时尚\"。
暮色渐浓时,街角修收音机的老师傅点起一盏白炽灯。昏黄的光晕里,整条街忽然生动起来——褪色的招牌在墙上投下影子,像在上演皮影戏;远处传来叮叮当当的炒锅声,间或飘来几句粤语笑骂。我想,所谓城市记忆,大约就是这些声音与光影熬成的老火汤。
离街时遇见个卖麦芽糖的阿婆,硬塞给我一块,说后生仔要多尝甜。糖很粘牙,却意外地好吃。忽然明白,这街就像这块糖,看似不合时宜,内里却藏着化不开的滋味。愿这些承载着城市心跳的老地方,能在时代的牙缝里,找到自己的活法。
[1]此处化用《祝福》开篇笔法,通过新旧对比营造时空纵深感
[2]暗引《阿Q正传》中\"银桃子\"的意象,喻指被时代淘洗的旧物
[3]借鉴《故乡》中闰土认\"我\"老爷的细节,表现代际认知差异
[4]挪用《社戏》中乡民看戏的场景描写手法
[5]结尾呼应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的\"
发布于:山西省景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